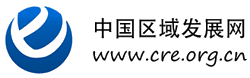区域政策
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本质与疏解方向时间: 2016-10-08信息来源:张可云 作者:hjr_admin 责编:
作者简介:张可云,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自2014年明确提出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以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就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特别是在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后简称《规划纲要》)的要点公布之后,学术界虽然高度认同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对于如何理解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并没有形成共识。虽然疏解工作已经部署,但目前对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认识依然存在误区,从而影响了社会各界对疏解重点、方式与方法的认识,这不利于顺利推进疏解工作。
“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在《规划纲要》中反复出现,表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中之重。《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优先重点疏解四类非首都功能:一是一般性产业特别是高消耗产业;二是区域性物流基地、区域性专业市场等部分第三产业;三是部分教育、医疗、培训机构等社会公共服务功能;四是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和企业总部。但是,这只是对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列举,而非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全部,据此也无法确定具体的疏解对象。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术界围绕什么是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问题提出了许多观点。
目前,对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认识存在四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不符合北京“四个中心”定位的功能;第二,低端、低效益、低附加值的部门;第三,由非市场因素决定布局的公共部门;第四,低素质人口及其从事的行业。仔细进行逻辑推敲便会发现,这四种认识都存在一定的问题。
首先,北京的定位并不等于首都功能。科技创新中心是“四个中心”之一,难道任何科技创新都要集中在北京吗? 一些已经或将要退出北京的行业,如冶金、造纸等行业的研发中心并不一定非得集中在北京不可,否则北京的膨胀问题的解决将遥遥无期。因此,对科技创新中心这个功能定位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该进一步识别出其中哪些是非首都功能。
其次,北京要提升自己的全球竞争力,必须提升产业发展档次,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并不能否认与之配套的低端行业存在的必要性。任何一个城市不论其发展方向与性质是什么,都需要一定的生产性与生活性服务业相配套,这些产业有些不可能是高端的。
再次,公共部门的布局都不是由市场因素决定的。如果将由非市场因素决定布局的公共部门列为非首都功能,它们也得往其他地区疏解吗?这显然是不准确的。
最后,人口素质高低与文化程度没有必然联系。在生活中,文化程度与素质高低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而用素质高低难以确定哪些行业是非首都功能。
由上述分析可知,目前比较流行的识别北京非首都功能的一些认识都存在一定的误区。那么,到底什么是北京非首都功能呢?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搞清楚首都属性与城市属性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首都是一种特殊城市,其与其他非首都城市间的根本差异在于:其代表国家形象,且中央政府赋予其高级别政治地位。这两个方面便是首都属性。同时,北京又是一个综合性城市,具有一般城市所具有的普遍特点,如必须承担发展经济、提供就业、提供文明生活方式等功能。这些功能就是城市属性。首都属性决定首都功能,而城市属性决定城市功能。北京定位是指城市功能中那些决定发展方向的关键功能,包括四个方面,即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与科技创新中心。其中,只有政治中心与国际交往中心是首都功能。首都功能与北京定位相互影响,首都功能优先于北京定位,而且两者都不可能排除所有的低端部门。但两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 首都功能为必做,北京定位为拟做,因此北京定位不一定不是非首都功能。所谓必做,是指既然首都定在北京,那么北京必须成为政治中心与国际交往中心。所谓拟做,是指北京市的定位是可以研究与改变的。通常,城市定位会随着城市发展阶段与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建国以来,北京定位曾几经调整。2004年版的《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所确定的北京定位(当时的定位为国家首都、国际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与目前的定位就有很大区别。具体而言,北京“四个定位”中的文化中心与科技创新中心并非必然是首都功能,因而这两个方面的部分功能也可被列为非首都功能之列。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界定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内涵。所谓北京非首都功能,是指现有北京功能中与首都功能存在矛盾并妨碍首都功能发挥的那些功能,或者说是北京的首都属性对北京功能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具体而言,只要是会对首都功能的发挥产生潜在负面影响的北京功能都应该列入非首都功能,即便是属于北京定位中的一些功能也是如此。首都属性对北京功能所产生的负面影响需要作进一步解释,其具体含义是指北京依靠其独一无二的首都地位吸纳了并不利于首都功能发挥的功能,因而应该列为北京非首都功能。过分吸纳外地特别是河北周边地区的资源,导致北京本身膨胀与所在区域发展失衡,具体表现为北京发展规模过大且结构不合理,同时北京对河北产生的回流效应大于扩散效应,京津冀难以协同发展。
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在明确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内涵后,为了便于操作,还需要明确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外延。为此,笔者提出一个划分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方法。可以从北京定位与非北京定位两个方面确定非首都功能的外延。在北京定位方面,有两类非首都功能:与首都功能冲突的创新功能; 与首都功能冲突的文化功能。在非北京定位方面,也有两类非首都功能:制造业中的物理生产部分、“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功能;北京低端生产性与生活性服务业中的超额部分。下面举例说明这四类北京非首都功能。
并不是所有创新功能都不会与首都功能发生冲突。有些低端行业在北京已经不存在或即将搬迁出北京,其创新中心没有必要留在北京。如果所有行业的创新功能都布局于北京,北京就永远不可能“消肿”,因为这些创新中心本身虽然人口不多,但其“拖家带口”以及配套服务部门的人口众多。
同样,并不是所有文化功能都不会与首都功能发生冲突。具有北京特色的文化企业应该保留并进一步发展,但一般性的演艺团体、皮包公司性质的文化企业应该迁出北京。
制造业中的物理生产部分是指产业链中的低附加值与劳动密集环节,是相对专注于创新的逻辑生产而言的。例如,软件研发属于逻辑生产,而将软件制作成光盘属于物理生产。逻辑生产可放在北京,而物理生产可疏解出北京。“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功能会影响首都形象,是必须疏解的对象。
北京作为首都必须拥有完善的生产与生活服务功能,其中有些是低端服务业。低端服务业也是北京城市有机体正常运行的必备功能,但应该有一个度。低端生产性与生活性服务业中的超额部分必须作为非首都功能疏解,原因在于低端服务业集聚人口众多,过度发展这些行业必然会导致北京人满为患。
2014年以来,为了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北京市委市政府在发展方向、智力支撑、氛围营造、夯实基础、动力构造与外部环境建设等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规划纲要》提出了统筹解决好“搬哪些、往哪搬、谁来搬、怎么搬”的问题,在疏解对象、疏解原则、疏解方法、疏解方式与人口调控等方面提出了行动方向,但《规划纲要》仍然是方向性的安排,对具体疏解工作而言没有具体列出疏解对象,而且没有提出可供操作的具体措施。
根据前面的内涵与外延分析,未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思路应该是:区分国有与非国有企事业单位,有针对性地制定疏解措施,控制人口规模。
——针对国有企事业单位,应该强调两个方面的手段,即规划与行政手段相结合。对于被列入疏解名单的国有企事业单位,有必要使用行政手段令其在限期内搬迁。对于积极主动配合规划实施的单位,应该给予充分的奖励。而对于拒不执行规划的,可使用行政处罚手段,达到疏解目的。
——针对非国有企事业单位,应该采取有别于国有单位的措施。制定具体的奖励政策,促使非首都功能企业自动转移出北京,例如区域工资税折扣政策。这个政策的基本操作方法是,对集聚在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企业收取高额的工资税,并将收取的工资税用于奖励移出北京的企业。通过类似的办法,可以实现花较少的成本而转移非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目的。
——针对人口问题,可执行严格的最低工资法。人口集聚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产业集聚决定的,不能根据个人受教育程度,也不能根据所谓的素质高低,确定哪些人应该迁出北京。严格的最低工资法的优点在于,如果一个企业在北京付不起地方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则其无法在北京生存,迁出就是其唯一的出路。
总之,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将北京建设成为真正的世界城市的一个战略任务,对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也十分关键。要将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落到实处,需要集思广益,在《规划纲要》的基础上制定出具体的操作规划与细则,如此方能稳步推进疏解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