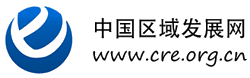经济增速过快“无助”国家竞争力?时间: 2015-09-01信息来源:赵广立 作者:dlj_admin 责编:
经济发展速度作为一国社会再生产状况和国民经济发展的综合性指标,往往被拿来衡量该国的发展水平。从人之常理来讲,高经济增速意味着更多社会价值的创造和社会财富的积累,似乎经济增速越快越有助于提高一国的国家影响力和竞争力。事实果真如此吗?
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研究项目“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基本要素和支撑系统研究”(以下简称“项目组”)的一组研究成果显示,国家影响力、竞争力与经济发展速度之间并非存在严格的线性关系,甚至呈现出一定的负相关;世界上主要的发达国家在历史时期其经济增速也并不处于高位。
经济增速与国家竞争力“逆向对应”
项目组研究成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成金介绍说,按照严格定义,国家竞争力是指一国在自由和公平的市场条件下,能够生产出满足国际市场需要的产品和劳务,同时又能维持和扩大本国人民长期的实际收入水平的程度。具体测算包括经济总量、经济效率、经济结构、发展潜力和创新能力等方面的若干指标。
出乎预料,统计显示,竞争力强的国家不一定具有很高的经济增速,具有较高增速的国家也不一定有很高的竞争力。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竞争力较强的国家主要分布在欧洲和北美地区,东亚一些国家和中东国家也在竞争力排名中居前。
王成金对这些国家的竞争力点数和GDP增长指数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竞争力点数以6.0为上限,竞争力大于5.0的国家中仅卡塔尔和马来西亚保持5.6%和4.7%中速增长,其他均保持低速增长或零增长甚至负增长,主要是欧洲、北美、澳新及中东等发达国家和石油国家。
反观经济增速分别为超高速、高速、中高速增长的国家,他们的竞争力点数均处于全球水平(4.2)以下,其中经济超高速增长的国家平均为3.53,高速增长国家平均为3.99,中速增长的国家平均为3.94,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值得一提的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中,仅中国保持较高的竞争力,点数为4.89,位列世界第28位。
王成金援引《全球竞争力报告》分析称,经济增速和国家竞争力两者之间之所以呈现出大致的逆向对应关系,主要原因是由于经济的超高速发展带来的其他问题,如民生问题、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等导致了国家竞争力的下降。
“强国”也曾经济高速增长
从历史上看,世界上具有较大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国家并非对经济的高速增长“不感冒”,事实上,在世界权力中心转移过程中,“退位者”往往具有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继承者”多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状态。
王成金介绍说,15世纪地理大发现后,欧洲国家开始崛起,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先后成为世界权力中心或某大洲具有影响力的国家。其中英国18世纪通过工业革命而经济迅速发展,经历过一段高速增长期,世界也进入了“英国时刻”。但此后直到权力中心转移至美国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英国的经济增速波动不大,基本保持在5%以下。
“一战”后世界权力中心由英国转移至美国,进入“英美时刻”。在此期间,美国经历了周期性的快速增长与快速下降过程。二战之后,美国成为最强大国家,经济发展却进入了中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时期。美国仅有的一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发生在1934~1944年,该时期恰是世界权力中心由英国向美国转移并由美国掌管的时期。
其他在“国家客观影响力指数”排名中位居世界前列(据中科院现代化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2013年前十名分别为美国、德国、法国、英国、中国、日本、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和加拿大)的国家中,在形成了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之后的经济增速普遍不高。
佛罗里达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访问学者、现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孙东琪也是项目组一员,他提供的一组研究数据显示,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属(超)高速增长模式,之后为中低速发展模式;欧洲多数发达国家则在工业革命之后长期处于中低速发展态势;加拿大在达到我国人均GDP水平之前的二三十年内里已变成经济中低速发展,之后的发展经济增速也同样不高。
“国家影响力、竞争力与经济发展速度之间并非存在严格的线性关系。”王成金总结说,“但国家影响力、竞争力需要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进行支撑,尤其是国家影响力、竞争力的培育、强化提升阶段仍需要中速的经济增长提供支撑。”
经济增速下降是低端产品转型升级的必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经历了长时期的高速和超高速增长,按照购买力水平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从国家竞争力排名到国家软实力对比,我国综合竞争力还不够理想,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也让中国经济增速面临巨大压力。
事实上,“从‘十三五’开始,我国应当谋求多高的经济(预期)增长率”在学术界和社会人士中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不过,在项目组成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唐志鹏看来,中国低端产品“世界工厂模式”的转型升级势必带来经济增速的下降。
“国际市场需求整体低迷的背景下,钢铁、造纸、电解铝、平板玻璃等主要资源型产品制造行业投资扩张的步伐仍然较快,产量持续增长,对全国经济转型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唐志鹏认为,未来产能过剩带来的供需矛盾可能会随着全球市场低迷而进一步加剧。
紧随而至的危机,是创造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正在并将逐渐消失。项目组另一成员、中科院地理所助理研究员宋涛指出,近几年,许多相对低端的制造产业纷纷转向劳动力成本更具优势的东南亚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外贸出口面临着低端被“蚕食”、高端“上不去”的尴尬局面。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等传统经济高速增长的推动力量逐渐减弱,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必然会有所降低。”宋涛说。
唐志鹏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长期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得我国的经济增速与能源消费增速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他认为,在节能减排的政策影响下,“以量取胜”的粗放型出口转向“以质取胜”的低碳绿色出口,也决定了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必然会有所降低。
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指出,我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已是必然趋势。进入中速经济增长,将为建设经济强国和实现我国和谐社会提供重要的机遇和空间。陆大道指出,中速增长是年增长率在6%至4%之间的增长。进入中速增长既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反映,也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中速增长对于我国的今后发展是“精明增长”“佳好增长”,是通向世界经济强国的增长。